
00
急雨打青檐,马蹄声自官道上踢踏而来。
枣红马上的骑士压低斗笠,利落地翻身下马,在驿店前拴了马,靴踏雨雾,一径行入店内。
店家勤快,早已预料到有雨,挂起了沉重的桐油布幔,店内空气混浊而温暖,不少身着短打的过路客正在嬉笑吃喝。
戴斗笠的武者环视一眼,抱臂坐在墙边,店小二殷勤指点水牌:“客官用些什么?”
武者摇了摇头,自怀中掏出一块玉璧,璧形如梅花,莹光内蕴,隐约透着美人纤指般的淡粉色泽,小二不禁瞪大了眼睛。
武者的帽檐压得低,看不清面容,但人人都能轻易听出他语调中的疲惫:“我来找一口泉眼。”
正在柜上打算盘的老掌柜闻言,感慨地抚了抚颔下白徐:“客官是来找‘灌园泉’的吧?好久没人打听过了。”
武者点了点头,手指紧攥那枚玉璧,小二本想问问他,能否借给众人看个稀奇?见他如此视若拱璧,当即很有眼色地闭上了嘴。
世传有一灌园老叟,爱花成痴,甚至感动了花神,老叟虽逝,花神点化过的泉水却仍在灌园旧地流淌,尽管今x此地已成魏巍山峦,但仍有爱花者前赴后继。
老掌柜放缓了语气:“客官也擅培花?”——————————阅读全文伽QQ❤:209152664,回复“1”获取资源—————————
若不是为了栽种珍稀花木,没有人会冒着生命危险进山寻找一口虚无缥缈的花神之泉。
武者再次颔首,掏出几块碎银,买下了猎人们绘制的地图。
不多时,雨散云收,武者马不停蹄地离去,店小二若有所思地搭在柜台边:“掌柜的,以前也有人进山找过泉眼吗?”
“自然是有的,那时京中以梅为最,京中贵人派出许多人手寻找,只为培出举世难得的梅花。”掌柜的揉了揉眼,接着打算盘,“可惜,可惜,最好的梅花还是只开在京城啊……”
可惜今人不知,艳绝京城的那一树梅花,已凋零五载。
01
京城最冶艳的一树梅花,最初开在护国公府,后来却迁到了教坊司,不得不说是一桩奇事。
至德十三年,护国公府因事涉太子谋反而被查抄,家眷或没入教坊为奴,或被剁掉了大好头颅。
事变时,谢清嘉刚画完一枝梅花。
他是家中最年少的公子哥儿,袭爵立业轮不到他,且家中长辈疼爱,一生注定富贵,便将十二分的心思都用在了风花雪月上。
前代老国公性喜藏书,家中琅嬛阁天下闻名,有诸般野史怪谈,这位小公子镇x埋首其中,不知从何处习得栽梅之法,能令梅花四季常开,疏影横斜,逸态超迈,更是画得一手好画,集为《梅谱》,每幅各有风情,譬如人之千面。
谢清嘉生得也像梅花,且是白茫茫雪中一枝梅,任是无情也动人。
他凝神提气,以俊丽小楷落笔题画:“琼姿只合在瑶台。”
一句诗方落,小印还未盖,抄家的官兵便涌入他作画的小楼,谢清嘉疑惑地抬首,出于自小的教养,行动端方,并未做惊惶之态,然而被人夺去手中笔,束上沉重铁链时,他仍是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
国公府的小公子,素来养在绮罗丛中,哪识风霜?
他面前的官兵皆嘻笑指点于他,又作揖向他道喜:“恭喜小公子,你可享福了,不用跟你那些叔伯兄弟们一起去边关吃土!”
闻言,谢家的侍从们皆面露耻辱神色,谢清嘉怔了怔,心下竟是一阵好笑——难道自己要被没入教坊司不成?
谢小公子的手腕上从未悬过比毛笔更重的物事,眼下却黑沉沉锁了枷,映衬着如羊脂玉一般的腕子,教人忍不住频频回望,押送他的官兵中,已有人开始窃窃私语——这般好颜色,身价几何?
谢清嘉却是半点不慌,整顿衣衫,安然坐于教坊司的拔步床上。
处处绮罗,壁染椒香,弄玉双成也住得,只是纱帐上绘着交颈鸳鸯,床前清供瓶中x的是合欢,怎么看都不像正经人该来的地方。
谢清嘉很笃定,有人会来救他。
那人没有让他失望,夜半时分,晋王匆匆而来。
“表哥!”谢清嘉急促起身,一见到可依靠之人,便忍不住x了眼眶。
晋王乃今上第五子,其母谢妃是谢清嘉母亲的同胞姐妹,护国公府正是他的外家。
谢妃性情柔糯,不大得宠,一味只知避世,好在晋王自小便顽劣,饶是有谢清嘉这样聪颖的伴读,也不见学出个子午寅卯来,因此没人把他们母子视为重大威胁。
如今谢家获罪,乃是因国公做主上了太子的船,欲行x宫之事。既是谋反,便做得极为隐秘,连宫中的谢妃都未告知,若不成功,她亦是弃子。
此时谢妃已昏厥过去,谢清嘉并不知宫中内情,打从一开始,他便和家人被迫分离开来,被带走时,抄家的官兵在他全身上下格外猥亵地摸索,甚至深入亵裤,轻佻地弹了弹他的臀瓣,谢清嘉自己都差点不出来,更别提用于贿赂的金银了。
他只能权且忍耐,强作镇静,然而一见到晋王,他便忍不住,急切地挽住表哥衣袖:“怎么还穿着朝服?刚从宫里出来吗……你有没有被迁怒?!”
虽然过得悠闲,但谢清嘉毕竟是世家子弟,有基本的大局观,祖父瞒着全家上下做定了这一件大事,要想全身而退是不可能的,眼下只能指望晋王,只有晋王先摘个x净,才能抽身对谢家施以援手。
谢清嘉自小被选入宫中,做晋王伴读,与表哥的感情比亲兄弟们更亲厚,他从不怀疑晋王的一颗赤子之心。
做伴读是件累人的差事,皇子们念错了书,挨打的总是伴读,晋王本不擅读书,但为了护着粉雕玉琢的小表弟,不让他挨打,x是x着自己头悬梁锥刺股,苦着脸越读越懵。
连谢妃这样绵软的性子看了都心疼:“实在读不进去就算了……你又不必和太子比,实在不行,让你表弟回家去,母妃再为你挑个沉稳些的伴读。”
晋王眼中晦色一闪而过,倒扣手中圣人言,仗着年纪不大,竟是撒起泼来:“我不!我就要表弟!谁敢撵表弟我跟谁急!”
话是这么说,可他还是记不住书,被罚时只得挡在谢清嘉身前,咬牙对太傅抱拳道:“表弟年纪小,禀赋柔弱,如何禁得起戒尺?我虽读书不通,倒是个皮糙x厚的,太傅还是打我罢!”
此话一出,当即引得全场哄笑,太子待他也更为宽和,私下玩笑道:“五弟倒是个怜香惜玉的,你这小表弟再大些,必是天人之姿。”
一个沉湎声色的皇子,构不成太大威胁。
晋王名刘钺,斧钺刀枪,煞气四溢,乃是今上随手捡的字,明摆着对这个儿子没什么兴趣。
然而他自己倒是很喜欢这个名字,曾捏着谢清嘉软软的小脸调笑道:“我命里煞气重,恰好缺一味药引,需得你这梅花来配。”
一刚一柔,两小无猜,谢清嘉被他护得几乎不知世事,若非天生灵慧,早成了他专属的匣中玩物。
及长,晋王独善其身,并不与朝臣结党,更不与皇子密切来往,除了舞枪弄棒之外,便是逗弄小表弟以为乐,因此这几年皇帝待他反而亲热了些——儿子不经比,太子等人越是勾心斗角地瞄着皇位,越显得这个儿子珍贵。
他生得俊朗,一双眼灼灼如辰星,谢清嘉一直笃定他非池中物,但无论他心中有几多丘壑,对着外人又是怎样威严,在谢清嘉面前,刘钺永远是温柔而略带怜惜的。
哪怕此刻身份有如云泥之别,也是一样。
晋王抬起手指,抚上谢清嘉脸庞,神态温存,谢清嘉见他舒展双臂,暗示自己为他更衣,虽然莫名其妙,但也心疼他在御前熬了一天,连忙笨手笨脚地替他除下朝服,叠在床上。
晋王的手指始终流连在他脸颊上,不管谢清嘉如何急切地追问事态,甚至略有不悦地闪躲,都不曾挪开手指,甚至顺着领口愈发向下,直摸到锁骨。
挣扎间,谢清嘉才发现自己已被x退到床边,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攫住了他,他面色发白,像一枝矜贵的梅,惨遭风雪打x,褪了颜色。
晋王高大的身形沉甸甸地将他覆盖,烛影中,一双人影渐渐重叠,凝固成比铁枷更沉重的锁。
晋王语调仍是温柔,眼中却多了谢清嘉未曾见过的神色,那是对着勾栏妓子才会有的神色:“去年有人送了本王一方芙蓉冻石砚台,颜色极为莹润优美……”
说这话时,他赤裸裸地望着表弟的锁骨。
谢清嘉唇上已被咬出血迹,他足够聪慧到明白眼前发生的事,但还不够坚强到接受这一切:“……表哥,你是来救我的吗?”
晋王笑了笑,一手抽掉他鬓上发簪,一手将他推入无边红浪中:“本王是来教你认命的。”
02
认命,对于勾栏院中的官妓而言,也算得上一种救赎。
谢清嘉认床,从前宫里的床他睡不惯,都是表哥搂着他睡,晋王将他牢牢抵在心口,温厚而坚定的心跳声安慰着他,哪怕有时他会发现表哥起了不该起的反应……他从未怀疑过表哥的用心。
然而他不再是谢家的小公子,他不过是擅画梅花的官妓,来嫖他的人,是晋王。
教坊司的床睡得并不舒服,被从小除了父母之外最信任的人活生生撕裂更不舒服,谢清嘉恍惚中只觉魂灵出窍,遥见天际一枝红梅凋谢,虬结枝条被人一斧斫断,汩汩渗出惨烈过朱砂百倍的血x。
晋王留了一夜,在嫖客中,算是相当耐心,抵着他腰臀将他完全撑开,教他下次该如何款摆天生的细腰,好留住客人,又教他:“哭可以,咬人就算了,不是人人都像本王这么宽容。”
说罢,晋王自己也觉得好笑,将染血的虎口抵在表弟脸上,语调亲昵:“你这咬人的毛病打小儿就改不了。”
谢清嘉脸颊高高肿起,乃是咬了贵客的下场,面无表情,眼泪却不由自主地流下。
他不明白晋王此时怎能谈笑风生地叙旧情,但他明白护国公府上下几百号人的命一定捏在对方手里。
因此第二x起身时,他已学得乖顺,跪在地上替晋王着靴,昨x连重物都没提过的手腕,今x已被掐出斑斑淤痕。
也许是从前做伴读时太骄狂,以致今x贱如靴底泥。
晋王一踢靴尖,挑起膝边美人面,含笑凝视,意气风发。
昨x太子被废,晋王母家被族诛,他于御前唱念做打一番,绝口不提自己的清白,只提自小与表弟亲厚,求皇帝无论如何要赦免谢清嘉。
他不为护国公府求情,连母亲可能哀痛欲死都不顾,自己也失了母家臂助,皇帝如何不信他的清白?
他又肯替谢清嘉求情,足证忠诚之外还有情义,皇帝明面上龙颜大怒,心中却对他格外高看了几分,杀尽谢氏全族后,开恩饶了谢清嘉一命——只是对护国公府的怒气犹在,因此没教他发配,而是阴毒之极地没入教坊司。
谢清嘉后来从恩客们口中渐渐拼凑出了事情的全貌,那时晋王已扶摇直上,没了劲敌,不必藏拙,他竟是个文武双全、面厚心x的狠角色。
外家败落,亦不可惜,蒙上皇怜惜,已给他赐了一门上等的好亲事,岳家会牢牢被绑在他的船上。
无论他自小对谢清嘉的关照有几分是因为需要个挡箭牌,好让太子以为他没有威胁性,他对表弟总归还有几分香火情——再不济,身为皇子,却要替一个伴读挨打,如此屈辱,化作滔天欲火亦是情有可原。
第一夜过后,他没待太久,只简短地告知谢清嘉两件事:第一,要想活下去,就听他的吩咐,周旋于达官贵人之间,做他的耳目;第二,他匆匆忙忙赶来凌虐了表弟一夜,乃是施恩,至少人人都知道谢小公子还是晋王的人,折辱也总有个限度。
谢清嘉跪伏于地,腰臀酸软,手肘无力,抬头时宛若瘦梅不堪风雨,默垂红泪,无声啜泣。
晋王叹息一声,在他额上一吻:“清嘉,这也是你的命。”
谢清嘉目送他潇洒地拂袖而去,泫然欲泣的妩媚神情渐渐冷透,手指死死抵入掌中。
刘钺笃定他是梅花,一味药引,只能治人,不敢求死。但刘钺忘了一件事,纵是药引,也是要在炉中焚烧沸腾的——
他当然不想死,他只想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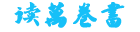 青苹果小说网
青苹果小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