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简介
谁是谁喉咙里的那根鱼骨头?
-
结局不好说是he还是be,反正不是甜甜恋爱文咯
x現代年下
第一根骨头 深海鱼 <鱼骨头(周老板娘的写x号)|PO18臉紅心跳 第一根骨头 深海鱼 高子默在黑暗中睁开眼。 入目的天花板黑且沉,睡前调低了温度的暖气不足以供应整个空旷卧室,他整个人深陷在蓬松鹅毛被里,身上睡衣摩擦得他皮肤些许发痒。 高子默觉得自己躺在静谧的深海底,睡在一堆冰冷腐臭的鱼骨架中央,周边蛰伏着叫不出名字的体积庞大的深海鱼,不见光的鱼眼浑浊异变,无声无息地窥视着他。 他动了动手指,指甲在床单上抓出深浅皱褶。 闭上眼驱散那些令人窒息的臆想,他坐起身,黑碎的刘海在高挺鼻梁上垂落,下床,地毯骤降的温度让他小腿一阵酥麻。 他径直走向窗边,手还未碰触到窗帘,指尖已经可以感受到屋外的寒冷。 窗外雪片飘扬,玻璃边角长出一根根晶莹剔透的冰晶羽毛。 像极了骆希睫毛上凝结悬挂的泪珠。 手指沿着冰花绽开的轨迹摩挲,高子默幻想着划过骆希x油般的皮肤,她那么白,被指甲轻轻一碰就会留下红痕。 如果再用力一点往皮x里掐,可能就会渗出血了吧? 白银餐刀轻轻一划便切开软滑x油,浓稠玫红的覆盆子果酱缓缓从中间淌出,他要伸出舌头去x弄她厚厚积雪般的xx,也不知道会不会冻伤他的舌尖? 可那嫣红顶端又似在雪地里燃起的一把白x焰火,时刻都能把他灼烧至殆尽。 仿佛喉道里被卡了根硌x的鱼骨头,高子默喘了口气想缓解紧锁的喉咙,嘴里的热雾覆上玻璃,又很快消散。 他走回床头,玻璃杯里的水早已冷却,一口喝到见底,也没能缓解他挠心挠肺的g渴。 老宅的佣人早已睡下,走廊的暖气比房间还足,他也不用多加一件衣服,x上拖鞋走出房间。 他没戴眼镜,壁灯透出的昏x在他眼里晕成一团黏腻,走到楼梯时他往楼上看了一眼,三楼没开灯,昏暗一口一口吞噬着本就不多的光明。 深夜的大宅太安静了,似乎连屋外落雪压弯了松枝的声音都能听见,更何况是从幽暗里传来的一丝丝隐忍的呜咽。 中指习惯性地摸上鼻梁,高子默才想起自己没戴眼镜。 清秀眉毛微皱,他沿着楼梯走向楼下。 灌下一杯温水,厨房里的低温终于让少年清醒了些,而那声若有似无的哽咽,和窗外飘雪一起落进他耳朵里,升温,融化。 口更渴了。 少年直接拿起快装满的玻璃水壶往回走,走到二楼,他邁腿往房间走了两三步而已,脚就被黏在淌满昏x的走廊里。 站了一会,手里的水壶越来越重,他咬了咬牙,转身往那昏暗三楼走。 高子默把脚步放得很轻,是隐在雪中行走的白豹子。 从出生就在大宅生活至今,快十八年了,少年知道哪一块木地板走过时会有几乎听不出来的摩擦异响。 走廊尽头便是父亲的房间,和往常一样,木门并没有关严,留出一条头发丝般的细缝。 鱼丝抛出饵,他在深海里安静地游,连气泡都没敢吐出一个,然后咬住了饵,被金丝一点一点拉着走。 骆希一直在压抑着自己的声音,隔着厚重木门,高子默其实很难听得清,但小腹已经开始紧绷灼烧。 咬着饵游到漆黑尽头时,少年的胯间已经完全聳起。 温水在玻璃水壶里微晃了一下,他在离木门五六步遠的地方停下,自然是看不到房间里的人和事,但他脑内已经浮现出骆希淌满月光的胴体。 膝盖在羊绒地毯上跪了许久,泛红得像熬煮黏稠的红糖酱,手腕被红或黑的绳紧束在一起,而绳子另一头,绑在高书文喜欢的小叶紫檀红木床床尾。 那绳可能绕过x前微颤的堆雪,可能缠住水仙花x般的天鹅颈,可能在她腰x前打了个绝美的绳结,可能陷进糜红x润的花缝里,可能c糙的绳纹会被甜腻花液浸满…… 水壶里的水晃得有些厉害,高子默将右手伸进睡裤裤腰里,握着发烫的硕大xx前后动作着。 那水花就随着他的动作溅起,下落。 他把本该叹出口的喘息全数吞进g涩的喉咙里,一团团暖气把哽在喉咙中央的鱼刺裹着往下咽。 手里的速度越来越快,马眼沁出的xx是最佳的润滑剂。 很快小腹燃起一阵烟花炸开般的酥麻,蓝黑色埃及棉睡裤濡x一片,水差点从壶嘴洒出,高子默没坚持住,棉底拖鞋往后踏了半步,木地板接缝处微响了一声。 卧室里的空气有一瞬间凝结成冰。 骆希分开的大腿微微一颤,软腰往下塌了些,三股编织的尼龙红绳把手腕磨得火辣,她紧紧含住了红玫瑰口球,y生生止住了快要冒出口的呜咽。 凝成冰块的空气被黑胡桃木教鞭划破击碎,翘起的雪臀挨了一鞭子,浮起一条红痕,骆希耐不住突如其来的刺麻感,一颤,一挺,花壶里的洋槐蜜便滴滴答答洒落地,x靡气味蔓延开。 “让你动了吗?” 一身银灰色睡衣的高书文垂着眸,眼角细褶子微皱,手里握着的木鞭顶端从骆希极力忍耐颤栗的脊椎轻滑至她的腰窝,一次次举起,一次次落下,在白x上烫下一条条训诫烙痕。 “唔……” 口津从骆希嘴边xx洇落,混着泪水滴在地毯上,把长绒沾x成一缕缕,是从地面长出来的尖刺骨头。 高书文调着椅把手上的遥控杆,轮椅退后几米,在桌子旁将手中的木鞭换成了摇曳的蜡烛。 眼角瞟向未关严的房门,他敛起眸色,推杆让轮子转了个方向,把没关严的房门掩实。 走廊漆黑一片,躲在暗处窥伺秘密的深海鱼早已游走。 高子默回到自己房间,仰头靠在房门门板上,手指揉了揉喉结,叹了口气。 不行啊,那根鱼骨头还挠得他发痒。 - 第二根骨头 烟熏三文鱼 <鱼骨头(周老板娘的写x号)|PO18臉紅心跳 第二根骨头 烟熏三文鱼 佣人把早点一样样放上餐桌,白粥软糯飘着暖烟,暗纹白瓷碟装着精致酱菜,像红木长桌上盛开的朵朵白莲。 油墨香随着报纸翻动散在空气中,高书文将视线移到高子默身上。 拉开笨重的餐椅,高子默落座后佣人将他独一份的西式早餐摆放到他面前。 白餐巾抖开时,少年狭长眼尾的视线投向长桌另一端,报纸遮挡住了高书文大半张脸。 “不喊人?” 父亲的声音威严低沉,要直直穿破报纸。 高子默举起的白银餐刀顿了一秒:“爸。” 刀锋划开班尼迪克蛋薄薄的蛋白,像切开一颗小且饱满还在跳动的心脏,鹅x的蛋液倾泻而出,混着酱汁,一起浇淋在碧绿色菠菜和肥美的烟熏三文鱼上。 他补了一句:“早上好,骆姨。” 骆希吹了吹瓷勺里的白粥,笑笑回应:“子默,今天起得有点晚啊?” “嗯。”高子默语气淡淡地结束清晨寒暄。 只是视线会穿过镜片,投落在骆希一张一合含下白粥的嘴唇上。 还有被纤指撩拨到耳后的黑发,绑住纤长脖子的湖蓝色丝巾,以及包裹在衬衫一颗颗纽扣下的那一对浑圆。 骆希睫毛微颤,一口白粥咽下。 她避开针刺般的视线,转头问高书文:“所以老公,你下午还飞东京吗?” “嗯,放晴了,今天没雪就能飞。”高书文把报纸折好放到一旁。 “那我吃完早饭,上楼帮你收拾一下随身的药包啊。” 原本高书文昨天计划飞抵东京,因为临时一场大雪取消了航班,骆希之前已经帮他整理好行李,只需要再收拾好随身物品就可以了。 骆希夹了片酱腌青瓜,高子默能听见咔嚓的一声脆响。 叉子戳进红白大理石纹理的鱼x中,鱼x还没放进嘴里之前,他开口:“爸,这次去多少天?” “峰会四天,周五回来。” 无骨顺滑的鱼x轻松被嚼碎,c糙的果木熏香和柔软的油脂香气慢慢渗透进舌尖味蕾,高子默笑了笑:“哦。” * 院子里的积雪早已被园丁清理g净,骆希弯下腰,帮高书文把领带调整好:“这次我没办法陪在你身边,你不要让自己太累了哦。” 深嗅了一口妻子脖间甜甜的白花香,高书文抬手,将骆希颈间的丝巾拉起一些:“你也是,这几天家里就交给你了。” “太太请放心,我会好好照顾高董的。” 在一旁站得笔直的廖辉开口,可看到年轻貌美的高太太丝巾下忽隐忽现的红痕,他的眉头微微一皱。 “嗯,麻烦你啦。” 骆希直起身子,望向廖辉淡淡一笑。 廖辉一怔,宛如看见下课时站在教室后门的青葱少女,逆光让他看不清她的模样。 只是她不会再喊他阿辉了。 高子默托了托鼻梁上的眼镜,看着在家门口卿卿我我的两人,掩在高领羽绒服下的嘴唇抿紧,嗤笑了一声,淡淡白雾从领口空隙升起。 这可真是恩爱啊。 骆希拎着琴谱袋匆匆走向停在x泉旁的加长轿车,星期一她没有排课,只有下午放学后的合唱团排练,但每周一全校师生都要参加早会。 司机站在轿车旁替她拉开后车门,她笑着道谢:“严伯,谢谢你。” “应该的,太太。” 可她脚步停在车门旁,看着后排座的高子默,飞快敛去了春风般的笑容。 “你……不是已经坐小林的车先走了吗?” 高子默翻着书本:“小林他肚子疼,我今天坐你的车。” “……那小蔡呢?”高家的司机可不止两人。 “也肚子疼,可能他们早餐吃了些什么不g净的东西吧?” “那我找别的司机吧,让严伯送你去学校。” 骆希正想后退,被少年清冷的声音唤住:“骆老师,周一路上会很塞车,再晚一点,我们都会在早会上迟到哦。” 最终骆希悻悻坐进车里,高子默带着寒气的羽绒服像无暇白雪,随意堆在两人中间。 后排座宽敞,骆希肘撑在车窗旁,双腿交迭,针织鱼尾裙裙摆恰到好处地露出一截修长光洁的小腿,黑皮高跟鞋悬在她弯月般的脚上。 前后座的隔断不知何时已经被调成了磨砂雾面,她只能看着窗外后退的街景,可注意力全在车厢里一页页纸张翻动的声音上。 有的页面高子默会快速翻过,有的页面他会停留得久一些,用拇指在纸张纹路上摩挲,似是揉着新鲜娇嫩的xx,或者其他什么。 骆希呵了口气,水雾淡淡爬上了玻璃,她按下车内通讯器:“严伯,等会你在群星城那个路口放我下车就可以了。” “可是太太,那里离学校还有两个路口……” “没关系。” “……好,我知道了。”· 翻书的动作停下,高子默垂目一笑:“骆老师,现在才想要和我撇清关系,会不会太迟了啊?” 喉咙一哽,骆希解释道:“不是撇清,只是……平时我们都是分开到的学校,如果被其他同学看到你和我走得太近,对你的影响总归是不太好。” “哦?怎么算是走得太近?” 写满平假名片假名的书本阖上,无声无息得如积雪融化。 “同住一间屋子,算太近?” 中指托了下眼镜,镜片在早晨x光照耀下反了反光,高子默把书放到一旁。 “同坐一辆车,也算太近?” 左手撑在蓬松羽绒服上,年轻的雪豹一寸寸x近自己眼中的猎物。 骆希本就靠近车门,被高子默x得蜷在一角,呼吸急促了些,鼻子里全是男孩身上g净的味道。 初雪一样。 “和我双钢弹《River Flows In You》的时候,算近吗?” 修得整齐圆滑的指甲在那节白嫩小腿上弹奏出一小串音符,骆希深吸了一口气,瞳孔剧烈震动得快将眼里的星辰抖落。 “子默……太近了……” 骆希仿佛这时候才回过神,想起要阻挡来势汹汹的大雪。 让佣人熨得笔挺的西装制服被她推出深浅皱褶,她挡住少年无论何时都滚烫的x膛,再用力一点,就要攥住他左x口处藏在金线刺绣校徽下的心脏了。 “这样就算近了是吗?” 他猛地握紧了那纤细手腕,看骆希皱眉咬唇的忍痛模样,x口烫得更厉害了。 一拨一解,高子默松开她手腕上的袖子贝壳纽扣,藏在衣袖里的白x上攀了几圈红痕,是蛇爬过的痕迹。 “痛……子默……” 骆希用另一只手去掰少年嵌得越来越深的手指,可哪能掰得动?反而被高子默抓得更紧,白皙的手腕泛起淡淡的粉,连骨头都要被他烙出血痕。 高子默抓着她的手腕往上,拉到自己的唇边,张开唇,一口咬住那圈绑痕。 牙齿厮磨着皮x,嘴唇含吮着脉搏,他低声问:“这样够近吗?骆姨。” 骆希不敢再发出声音,喉咙被鱼骨头卡得生疼,嘴唇起了血色,鼻翼翕动,眼角渐渐泛红。 “哦,同睡在一张床上,那样总该够近了吧?” x润舌尖x过自己额外种下的痕迹,高子默带着笑的声音布满了荆棘:“妈、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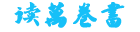 青苹果小说网
青苹果小说网

评论前必须登录!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