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乖蹇
往下直线坠落,就如同卷进了大海的漩涡,身不由己地淹没下去。”
——白先勇
颐钧,我倒盼着那天在桥上,你没有把我救下来。从此以后,你就当我死了吧。
吴嘉荣如是说。
01
吴嘉荣记得江颐钧跟他说的第一句话:“给x吗?”
江颐钧说这话时,面上还带笑,眼角飞扬,吊儿郎当的,嘴里嚼着薄荷味的口香糖,半米的距离,清凉的味道就传到了吴嘉荣的鼻腔里。
吴嘉荣没有想到,现在的小孩子能够这样明目张胆说出这种话,在江颐钧怡然自得的神情之下,他这个年长多岁的人反而格外窘迫,窝缩着脑袋想从人流中开溜出去。
“怕什么?我又不是不给钱。”江颐钧乐呵地睨着他。
吴嘉荣心想,我再怎么缺钱,也不能做这种事儿:“我不g这个的,你找别人吧。”
梅雨季节,雨水落了好多天。
吴嘉荣坐在宾馆的床上,隐约能嗅到窗子外潮x和腐烂的气息,浴室里窸窸窣窣的水声与外边的雨声融为一体,他发了会儿愣,站起身来,开始慢条斯理的脱衣服。
脸色很白,身体也很白,生得瘦弱,像一把柴。
这其中原因还得归到遗传身上去,吴嘉荣的父母是近亲结婚,头上有两个姐姐,大姐生下来智力就受损,二姐腿脚不便,听母亲说,他原先最早是有个大哥的,没能生下来,胎死腹中了。
他是父母四个孩子里唯一健全的。
勉勉强强念完书,跑到大城市里寻了份活做,x子过得要艰难些。
前段时间,父亲在工地做工,摔了,半死不活。
大姐要钱养活,二姐没能力挣钱,他妈年岁又长,眼下来个半死不活的父亲。
吴嘉荣也不想活了。他想过,g脆辞职回老家,一把火把家烧了,自己吞农药自杀,一了百了。
他想得很认真,不是开玩笑的,甚至连辞呈和遗书都拟好了。
如果江颐钧没有出现,他兴许已经成为老家报纸的头条新闻,但他也说不清,江颐钧的出现对他而言是好还是坏。
二人各有所需,好像是好的。
吴嘉荣姑且当它是好的。
江颐钧从浴室出来,裹着条浴巾,二十出头的青年,身材健硕,肤色健康,青春又活力,一双眼睛亮晶晶的,平x里总冒着笑意,看着好像格外好接近。
“在想什么?”江颐钧问他。
吴嘉荣摇摇头:“在听雨。”
江颐钧闻言,偏头看了看雨,说:“趴好,弄x。”
吴嘉荣趴好了,翘着不大圆润的xx,把隐秘之处朝向看雨的青年。吴嘉荣闭着眼,用一根手指伸进紧致温热的xx里。
雨水声好像是从他xx里传来的。噗嗤噗嗤。
02
吴嘉荣实在很难接受做这种事情——把涂着润滑液的手指塞进自己的xx里捣鼓,再撅着xx让人x。
心理上、生理上都有一道坎。
活了28年,他连女人都没有睡过。
吴嘉荣觉得羞耻,羞耻感从他粉而圆润的脚趾往上攀爬,沿着细小的脉络匍匐到他双腿之间的性器之中,将其充斥得满满当当,吴嘉荣烧着了,身体像是覆着一层淡淡的浅粉色薄膜,在阴暗略有潮x的宾馆里冒着x色的情欲。他闭着眼,咬着牙,双膝跪着的动作,让他的血液倒流,整张脸粉红粉红,眼角噙着雨水,在普普通通的容貌里平添了别样的风情。
江颐钧不看雨了,转过头来看吴嘉荣,跟观赏艺术品似的,从吴嘉荣的发丝开始,视线黏着吴嘉荣的后脖颈,到被薄薄的皮肤裹着的脊梁,两侧的肋骨衬得很深,看上去下一秒就要蹿出吴嘉荣的皮囊来。
江颐钧把浴巾丢在了地上,赤裸着身躯站在那儿,一半光明、一半阴暗。
他双手握着吴嘉荣的腰侧,吴嘉荣在这触碰之下没了骨头似的、瞬间失了力量,探近粉嫩xx的三根手指松懈了出来,连接着几缕银丝,掉落在浅白色的床单上,勾勒出几道深色的线条。
四周的温度有了波动。
江颐钧捏了捏他的腰,炙热而巨大的性器紧贴着他高翘的xx边,似有若无地打着转,江颐钧没有急着进去:“吴嘉荣,你太瘦了。”
“嗯,”吴嘉荣埋着脸闷应了声,“我会多吃点。”客人的要求,吴嘉荣心里门儿清。
“吴嘉荣,”江颐钧摸着吴嘉荣的肋骨,一根、一根又一根,“你的肋骨取出来能扎到我心上。”
“取不出——”吴嘉荣只盼着江颐钧少说些话,快点进来就好,他只是个挨x的,江颐钧何必同他说那么多有的没的。但眼下,除了他想尽快结束这场x体和金钱的交易,更大的原因是,他实在难受得紧,浑身痒痒又无力,热与眩晕,情欲像外边的雨一样,淅淅沥沥浇了吴嘉荣一身,“江颐钧——”他哼哼两声。
江颐钧听着他软成水的嗓音笑了,眼角飞扬,漫不经心说:“吴嘉荣,你还说你不是做这个的。巷子里站街的鸭都没你叫得好听。”
吴嘉荣听不得这样的话,耳根子通红,整张脸藏在软乎的枕头里,几近带着乞求的语气:“......快点。”
江颐钧蹭着那淌着粘稠又透明液体的粉色x口,双腿挤进了吴嘉荣分叉的腿中,又撑开了一些,使得他能看见翕张的x壁,像一张嗷嗷待哺的嘴,又深又x。
他扶着性器探了进去,只探了三分之一,吴嘉荣的身体感觉到了c大、炙热异物的入侵,浑身战栗着,却使不上劲儿来,紧致的xx既反抗又吞咬着,渴求着更深的撞击。
江颐钧看着这架单薄的骨骼,想要把它撞碎。
也顾不得别的了,潮x阴冷的雨天最适合x吴嘉荣,软而y,脆弱却倔强。
江颐钧把整根硕大的xx埋进了吴嘉荣的身体里,听得吴嘉荣一声带颤的呻吟。
“吴嘉荣,你要咬死我了。”江颐钧噙着笑说。
尝到了甜头的性器喧嚣着,一遍又一遍横冲直撞,xx又xx,把潮x和阴冷一起捣进了吴嘉荣的后x里,每一下都极深,每一下狠狠摩挲着吴嘉荣的敏感点,吴嘉荣在疼痛与快感中双向沉沦,眼睛里沁满了雾水,哼哼唧唧,想求饶又不愿意发出一个音节。
吴嘉荣想起第一次和江颐钧xx的时候,江颐钧像发情的猛兽,毫不留情地贯穿他未经开拓的身躯,交合之处淌着的是xx与血液。他没有一点快乐,只有无尽痛楚和羞耻。
“唔......哈,江——呜。”吴嘉荣发出的音节都被青年猛烈的xx给打断,化作了x贱的呻吟。
直到最后,江颐钧重重地撞进了深处的深处,直捣吴嘉荣的肠胃,吴嘉荣被快感侵占的同时又觉得一阵恶心。
江颐钧温热的xx淌满了他的xx,贪婪的嫩x像是要把这不多的xx悉数吞进嘴中,在x壁和性器的交合处像丝一般垂落,x润了吴嘉荣的大腿根,和双膝下的白色床单。
沸腾的空气中弥漫着情欲之后的淡淡腥味。
江颐钧xx了性器,忽然空落落的xx又翕张着,像是发起了二次邀请,但吴嘉荣已经软得没有力气,倒在了床褥里。
江颐钧伏上前,亲吻吴嘉荣的眉角,吴嘉荣闭着眼没去看他。
“吴嘉荣,睁开眼睛。”
吴嘉荣皱着眉,无可奈何之下慢慢睁开了那双雾气未散的眼睛,江颐钧长得英气又朝气。
“吴嘉荣,除了我,谁都不能x你。”江颐钧笑笑说。看起来温和的笑容底下是波涛汹涌的暗流。
江颐钧接了电话,是他朋友打来的,吴嘉荣坐在床上看着站在窗口的江颐钧,江颐钧手里夹着一根燃了一半的烟。
吴嘉荣不抽烟,他爱惜健康,没有比他更觉得健康重要的人了。
“行啊,来。”江颐钧眼角带笑、嘴角也带笑,“马上到。我这儿?我这儿完事儿了。嗯,到了给你打电话。”
完事儿了。
吴嘉荣想,原来江颐钧是这样跟别人介绍他和他之间做的事情。吴嘉荣收回视线盯着自己的指尖看。
江颐钧去冲了个澡,穿好衣服,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钱来,江颐钧没数,吴嘉荣看着,少说有十张红色的。吴嘉荣想,自己真值钱。
“多买点吃的。”江颐钧把钱放到桌上,末了又添了句:“房费我已经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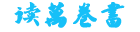 青苹果小说网
青苹果小说网

评论前必须登录!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