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不识(总攻/NP)
作家:霜晨月
原创 / 男男 / 古代 / 中x / 正剧 / 美攻强受 / 美人受
蒙冤入狱的谢问某一天被一个神秘人救出,然而他得到的却是一个匪夷所思的命令——保护一个来历不明的傻子丑八怪!?
这年头,在走心总攻NP文里当个主角真不容易,三个受君一个傻得掉渣,一个冷若冰霜,剩下一个暴脾气一登场就把老攻打得满地找牙。即便如此,也要咬紧牙关,坚强地左拥右抱。
走心总攻NP文 养成系VS美强惨VS小狼狗,1攻3受。乱世,英雄与美人。
阅读须知:
※1攻3受,结局大团圆1VN,xE
※作者口味奇特,热衷NTR,贵圈真乱,攻受无节x菊不洁等狗血桥段,虽然这篇文里面没有NTR,攻受菊不洁之类的桥段设定,但是会出现一些类似于NTR倾向的梗(有读者这么吐槽的),所以敬请各位感情洁癖/只能接受1V1/无法接受受或攻被戴绿帽的盆友自动避雷
※正剧向,架空历史,不要较真考据
※请不要问作者某人到底死了没有,问就是大团圆1VN你懂的
※本文为「红杏枝头」的外传。
总攻:谢问
总攻的CP们:谢琞/阿朔、皇甫轲、闻辛
其他配角:为夷、长风、成渊……
1 罪人vs丑八怪
楔子
深秋一场雨,将大虞国都城洛阳城中的银杏叶打落了满地。清晨时分,霜露正浓,城中西南角的琵琶巷中,一个身着青袍小杂花公服,年纪约摸四十岁上下的中年男子迈着匆匆的脚步,在那x缎子般层层叠叠的银杏叶上踩过。七拐八弯的深巷尽头是一堵爬满了青苔的巍峨高墙,探出墙外的寥寥几支枯枝上伫立着三两只乌鸦,高墙正门匾额上用遒劲的笔锋书写着留台二字。
留台,又称乌台,形似大户人家的深宅大院,实则为大虞国中一座特殊的牢狱,被囚禁在这里的不是普通犯人,也非犯了罪的朝廷重臣,而是被下了诏狱的皇亲宗氏。
中年男子从怀中摸出一块令牌,出示给把守在门前的两名侍卫。
令牌上是敕令二字。
侍卫看过令牌,毕恭毕敬地将中年男子迎进了高墙之中。
中年男子跟随着狱卒长穿过守卫森严的前厅与中堂,径直向西北角的狱亭走去。推开笨重的大门,迎面照壁上白底黑字地写着一个大大的狱字。照壁后方的院落中,一条阴暗潮x的石阶向下延伸,直通地下囚室。
一走入地下,中年男子便不由自主地蹙眉,这暗不见天x的地下囚室被一格格铁栏分隔成一间间个室,个室里除了一张床以外空无一物,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霉味与铁锈味。其中最大的一间囚室里的床上侧躺着一人,那人双目紧闭,单臂枕在脑袋下方,似在熟睡。中年男子走上前去,仔细打量起那男子的面孔,只见那人约摸二十多岁,是个青年的模样,面容清瘦,下巴胡渣丛生,衣衫虽然脏兮兮的似乎很久没洗,但料子倒是上好的丝绸。
“你就是淮南郡王世子,谢问?”
肃杀的声音在石室中空d地回响,压抑的沉默几乎令空气凝固。过了半晌,躺在床上的青年缓缓抬起眼帘,露出一对如潭水般深邃的眼眸。
“是又怎样。”名为谢问的青年瞥了中年男子一眼,便又无动于衷地闭上眼睛,慵懒地答了一句。
中年男子没有接话,而是俯首过去与狱卒长悉悉索索地说了些什么。谢问漠不关心地闭目养神,忽听哐啷一声,铁门应声而开。
“罪人谢问,起来,跟我走。”
雨后初晴的早晨,对于被囚禁了一年多的谢问来说,本应清冷柔和的阳光也显得如此刺眼。他没想到自己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带出了留台,中年男子没有一句解释,两人一前一后地行走在洛阳城中。谢问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个中年男子是谁,要带自己去哪儿,时值十一月初,秋风萧瑟,谢问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薄的锦袍,可他丝毫不觉得寒冷,反而贪婪地呼吸着许久没有接触过的新鲜空气,享受着重见天x的惬意。
当两人在洛阳南门被侍卫拦下时,中年男子再次出示了那枚敕令,走出城门后,满腹疑问的谢问终于忍不住开口:“你要带我去哪儿?”
中年男子转过身来,一脸严肃地看着他:“从今天开始,你自由了。”
谢问微微睁大眼睛:“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救我?”
中年男子头也不回地道:“我是谁并不重要,我救你自然不是无缘无故,而是要你去保护一个人。”
谢问还要再问,忽听身后马蹄声响,一队禁军装束的人马浩浩荡荡地直奔城门而来。中年男子脸色一沉,一把抓住谢问道:“不好,追兵来了,快跑!”
谢问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被中年男子拽着躲进路边的树林中,谢问一头雾水,小声道:“喂!什么追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年男子捂住他的嘴,压低声音道:“别问这么多!你只需记住一件事,你要保护的人在广化寺,名叫阿朔,你的任务就是保护好他,找到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切记千万不要回洛阳。”
说话间,禁军队伍已闯进树林,两人藏身之处身后是一条隐蔽的山沟,山沟底部长满了杂木乱枝,耳听马蹄声越来越近,中年男子不由分说地双掌齐出,将谢问从斜坡上推了下去,他居高临下地看了沟底一眼,随后扭头离去。
谢问狼狈不堪地从沟底爬起来,刚要骂人便听到上方兵器相交之声骤起,厮杀声中依稀能听到中年男子的怒吼。
谢问摇摇头,心想这男人必死无疑,果然,厮杀声很快便平息了下去,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低沉的声音:“还有一个人!给我搜!”
若是在以往,区区禁军谢问自然是无所畏惧,不过此时对方全副武装,人多势众,而自己却孤身一人,手上连一把像样的武器也没有,这时候冲出去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己好不容易出了大牢,可不能就这样自投罗网。于是谢问赶紧在灌木丛中躲起来,屏息凝神地观察着上方的动静。
大约过了一刻钟,在附近搜索了一番却一无所获的禁军终于离去。寂静的树林之中只剩下凄冷肃杀的风声,谢问又等了一刻钟,确定四下再无动静之后才蹑手蹑脚地爬了出来。
斜坡上方不远处,一人面朝下地倒在血泊之中,一动不动。谢问走上前去将那人身体翻过来,赫然正是那救他出狱的中年男子。
谢问心情沉重地伸出手去,探了探男子的鼻息,果然已经没了出来的气。谢问在那人身上摸了摸,想从他身上搜出什么能够辨明身份的物事,摸了半天只搜出一枚腰牌,从形制上来看似乎是宫中之物,除此之外便没有更多线索了。
面对着无名男子的尸体,谢问心中忽然升起一丝愧疚。虽然他与此人素不相识,也不知道此人救他到底有何目的,但是此人将他带出留台,并且为了掩护他而死也是不争的事实。滴水之恩也应涌泉相报,更何况是救命之恩。
谢问将男子就地掩埋,双手合十地在那隆起的土堆面前深深鞠了一躬。
秋风飒飒,席卷着残叶扬起谢问的衣角,此时的他并不知道,无名男子就像一颗投入宁静湖面的石子,打破了他本被注定的人生,更不会想到这毫不起眼的涟漪最终会形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切卷入波谲云诡的漩涡中去。
出了树林,往南走出几里地,便能看到一个小小的村落,四五间农舍散落于阡陌之间,一条清澈的河流从村中潺潺流过。
刚一进村,谢问便随便逮了一个路人问广化寺怎么走。被他逮住问路的是一名十五六岁的少女,一看到谢问便吓得花容失色,谢问这才意识到自己刚刚出狱,光看外表估计跟山里跑出来的野人没什么两样,当下毕恭毕敬地对那少女鞠躬赔了一礼,称自己是从他乡逃难过来的难民,问是否可以借地稍作休整。
少女起初确实害怕,但她见谢问说话条理清晰,似乎是个知书达理之人,况且此时天下初定,战火未歇,加之天灾连绵,流民难民的确不尽其数,这少女心地淳朴,便也不疑有他,爽快地收留了谢问。
总算找到了落脚之地的谢问先是跳进村旁河里痛痛快快地洗了一澡,搓尽满身满脸的脏泥,随后来到少女家中换上一身g净的衣服,刮掉乱糟糟的胡渣,将一头散发打理g净,整整齐齐地束了起来。此时少女已经为谢问热好了一笼包子和一碗小米粥,端着碗筷刚走进来,一见谢问便怔住了。
“公、公子……你,你……”少女盯着谢问的脸,瞠目结舌起来。
谢问扬了扬清逸的眉梢,微微一笑:“姑娘有何吩咐?”
“不,没什么……你,你请便。”少女满脸通红地放下包子和小米粥,竟扭头跑走了。
谢问对这种场面早已司空见惯,他不以为意地坐下,抓起包子就着小米粥大口大口吃起来。
吃饱喝足后,谢问向少女表达了谢意,顺便请教了广化寺的方位,得知广化寺就在村口西边的山上之后便告辞而去。少女与他说话时一直不敢用正眼瞧他,临别时却又依依不舍地把送他到村口,目送着他的身影消失在山间小路之中。
谢问没有花太大工夫便找到了广化寺。然而他并不知道几十年前的一场灭佛运动把广化寺毁去了大半,寺庙中的佛像被尽数捣毁,如今只剩下残垣断壁和一间破败不堪,满是灰尘与蜘蛛网的偏殿。
这样的地方会有他要保护的人?谢问将信将疑地推开偏殿的大门,一个人影嗖地从他面前一闪而过。谢问警惕地迈步走了进去,环视一圈,整个偏殿里空空如也,只有角落里杂七杂八地堆着一些桌椅杂物。
“有人吗?”
谢问响亮的声音回荡在空荡荡的殿内,但并没有人回答。
(那男子叫我保护的人叫什么来着,对了,好像是叫阿朔?)
想到这里,谢问开口道:“阿朔?你在吗?有人告诉我你在这儿,让我来这儿找你。”
话音刚落,杂物堆里一个脑袋小心翼翼地探了出来,一双如墨似漆的剪水明眸滴溜溜地盯着这边,目光中满是好奇。
想必此人就是那个阿朔吧。谢问不自觉地被这双眼睛吸引住,他没有走过去,而是蹲了下来,像逗小猫小狗一样冲那人挥了挥手:“你就是阿朔?”
“我是阿朔,你又是谁?”
一个有些稚气,但又如同山泉般澄澈通透的嗓音从杂物堆中传来。
谢问一愣,半晌才回过神来,回答道:“我叫谢问。”
“你是坏人还是好人?”对方又抛出了一个天真的问题。
谢问不觉失笑,心想也不知这名叫阿朔的人多大年纪,说话如此稚气,怕不是个孩子,于是笑道:“我是来保护你的,当然是好人。”
这么说完,角落里便传来悉悉索索的响声,杂物堆里爬出一个人,那人笨手笨脚,整个身子还没完全出来,就听到哐啷一声巨响,堆积如山的杂物轰然倒塌,那人“哎哟”一声被压在底下动弹不得。
谢问赶紧上前搬开倒塌的杂物,拽着那人的胳膊把他拖了出来。名叫阿朔的男子一边呜呜叫痛一边抬起头来。他不抬头还好,这一抬头可把谢问吓了一跳。
枯x的脸上坑坑洼洼没有一处好皮,塌陷的鼻梁下两个鼻孔朝天翻着,杂乱的八字眉下两只眼窝深深凹进去,颧骨却不自然地凸起,活像一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癞皮狗。饶是谢问见多识广,也从来没见过长得如此丑陋不堪的人。这要是夜晚寻到此处,谢问绝对会以为自己活见鬼了。
即便如此,谢问还是很有涵养地保持了处变不惊的态度,他定了定神,拍拍阿朔身上的灰尘:“阿朔,你没事吧?”
阿朔捂着后脑勺,眼角xx泪花,咧着嘴巴哭道:“阿朔的头破了,阿朔要死了。”
谢问大吃一惊,连忙拿开他按在后脑勺上的手一看,哪里有什么血,不过是肿起了一个大包。谢问松了口气,把手按在那包上揉了揉:“没事,头没破,死不了。”
阿朔只觉得脑壳痛,哪里信他,依然扯着嘴角哭。谢问有些不耐烦:“别哭了,你本来长得就丑,再哭更加像癞皮狗了。”
阿朔更委屈了,抬起一双泪汪汪的眼睛望着谢问:“你胡说,阿朔才不是癞皮狗!”
说来也奇怪,阿朔虽然人长得丑是丑,但那一双眼睛却是澄澈透亮,目中似有星辰。再加上那一副高山清泉般轻盈动听的嗓音,若是给他戴上一副面具,只露出一双眼睛,绝对没人能想象得到他会是一个丑八怪。老天爷实在奇怪,怎么偏生就把一双摄人心魄的眼睛和一把仙音似的嗓子给了这样一个丑八怪呢?
“好了好了,你不是癞皮狗,你是阿朔。可以了吗?”谢问拉着他站起来,“你先告诉我,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在这里?”
阿朔抽抽搭搭地吸着鼻涕,一脸懵x地看着谢问。
谢问一看不行,便掏出从中年男子身上搜出来的腰牌,对阿朔道:“有人要我来保护你,这是他身上的腰牌,你可认得此物?知不知道那人是谁?”
阿朔呆呆地看了那腰牌半晌,忽然伸手抓住,把腰牌凑到嘴边啃了啃。
谢问看他一问三不知的模样,心中有点着急,一把抓住他的肩膀晃了晃:“那你至少告诉我,是谁要害你?我连敌人是谁都不知道,要怎么保护你?”
阿朔被一脸凶相的谢问吓到,不知从哪儿生出一股力气,猛地推开他,跑到角落里躲起来,抱着膝盖瑟瑟发抖:“坏人!坏人要杀我!”
谢问无力地叹了口气。这阿朔看上去年纪与自己差不多大,身上锦衣玉带,一看就是富家公子,可是行为口吻却如同痴儿,除了自己的名字以外,竟是对什么事都一无所知,如果不是天生智力有问题,就是脑子受了什么刺激,成了傻子,搞不好还有失忆的可能。
联系到今天禁军搜捕那中年男子的情形,谢问不由得暗暗叫苦,自己怕不是牵扯进了什么天大的麻烦之中。本以为好不容易逃过了牢狱之灾,谁知又一脚踏进了一个未知的泥沼。
一想到这里,谢问不禁心乱如麻,一个转身走出了殿外。走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正这痴儿又不认得他,更与他无亲无故,是死是活与他何g。
然而走出几步之后,他又停了下来。自己真能这样一走了之吗?中年男子临死前的殷切嘱托犹在耳边,他真的要做他最为不齿的背弃弃义之人,丢下这傻子丑八怪,一个人逃之夭夭么?
就在这时,谢问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似的俯xx去,把耳朵贴在地上。由于长期跟随父亲淮南郡王征战四方的缘故,他练就了绝不逊色于斥候的灵敏听力,把耳朵贴在地上就能听出多远距离外来了多少人马。从他所听到的声音来判断,禁军似乎又来了一批追兵,而且已经到了山下村落,这广化寺只剩残垣一片,根本不是藏身之地,再加上他依然手无寸铁,这种时候若是遇上了禁军的追兵,不要说阿朔,恐怕连他都是x翅难飞。
当下谢问也不再多想,推开殿门闯了进去,冲到角落里一把抓住阿朔的胳膊。阿朔刚刚平静了些许,乍见谢问突然撞开门凶神恶煞地冲进来,又吓得屁滚x流,手脚并用地便要逃跑,一边爬一边叫道:“小凳子,小凳子!”
“什么小凳子?”谢问满头问号,不过他没空跟这傻子废话,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扑上去伸手一拽,将阿朔的一条腿扯住,阿朔被他拖住,只能手舞足蹈地在地面上乱爬,谢问看得只想笑,心想这癞皮狗难道是属乌龟的么,怎么这么喜欢满地乱爬。他大手一伸,啪啪啪地在阿朔身上点了几处xx,阿朔立马全身酥麻,渐渐停止了挣扎。
谢问二话不说地将阿朔拦腰抱起,走出偏殿,向寺外走去。阿朔在他怀中无法动弹,只能满眼惊恐地望着他,一张丑脸被近距离放大之后显得更加扭曲了。
谢问实在不想看他那张脸,只能把视线专注在那双明眸上,故意恶狠狠地道:“你给我乖乖听话,否则我把你扔在那破庙里,一会儿坏人进来就把你剁成x泥。”
阿朔吓得胳膊一伸,紧紧搂住了谢问的脖子:“阿朔不要变成x泥!”
谢问叹了口气,心道自己欺负一个傻子算什么事,于是轻轻拍了拍阿朔的脑袋权当安慰,提起一口气向山下飞奔而去。
2 乖,哥哥带你飞
谢问施展起轻功,风驰电掣地赶了几里路,不一会儿便到了山下的一个小镇,阿朔缩在谢问怀里,起初有点害怕,但渐渐地就被眼前飞驰而过的景色所吸引,兴奋得哇哇大叫。直到谢问把他放下,解开他的xx,他还拍着手道:“会飞的大哥哥,好厉害!阿朔也想学。”
谢问心想,以你的智商就别想了,嘴上却说:“你乖乖听话,大哥哥就教你。”
阿朔兴奋地用力点头,嗯了一声:“阿朔很乖的!阿朔听小凳子的话,也听大哥哥的话。”
谢问从刚才开始就想问了,此刻听到他又提起小凳子,便好奇地道:“小凳子是谁?”
阿朔却一脸天真:“小凳子就是小凳子。”
谢问沉吟片刻,心想这傻子说他听小凳子的话,这么说小凳子应该是他的监护人,而今天那个中年男子把他带出留台,拜托他来保护阿朔,这么看来,小凳子很有可能就是那个中年男子。小凳子什么的听上去像个仆人或者太监的名字,说不定那个中年男子就是宫里的一个太监。
谢问正一边走一边琢磨心事,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叫骂声,他一转身阿朔已不见人影,连忙环顾四周,发现叫骂声是从一个烙饼摊上传来的,摊主大娘正揪着一个人的衣领破口大骂。而那个被揪住的人不是别人,正是阿朔。
只见那大娘拽着阿朔的衣领一把把他推倒在地上,像赶苍蝇一样冲着阿朔挥手道:“去去去,小乞丐,滚一边去,别站在这儿挡着我做生意。”阿朔一xx坐在地上,眼眶红红的,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
谢问连忙上前将阿朔扶起来,对那摊主大娘怒目而视:“你怎么动手打人!?”
那大娘柳眉倒竖,毫不示弱,指着阿朔道:“这丑八怪小乞丐站在这儿,其他客人一见他吓得掉头就跑。而且他妨碍我做生意也就罢了,关键他吃了我的烙饼还不给钱。”
谢问大吃一惊,转头对阿朔沉声道:“她说的是真的?你没给钱就拿人家东西?”
阿朔委屈巴巴地抬头看他:“钱是什么啊?”
谢问心里忽然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买东西要给钱,你要吃烙饼,也得有钱才能吃,你有钱吗?”
阿朔摇摇头:“我不知道。”
谢问以手扶额,他忘了这家伙是个傻子,而且还是个连钱是什么,以及买东西要给钱这么天经地义的道理都不懂的傻子。不巧的是,谢问自己也刚出大牢,身无分文,就连方才在村里的那一顿都是在人家姑娘家里蹭吃蹭喝。他们俩一个傻得掉渣,一个穷得吃土,可谓是寸步难行,前途多难。
眼瞅着阿朔眼巴巴地盯着那热腾腾的烙饼不肯走,肚子咕噜咕噜叫个不停,谢问转念一想,问道:“你之前肚子饿了,都是上哪儿找吃的。”
阿朔咬着手指道:“都是小凳子给我的。”
谢问心道也对,这傻子锦衣玉带的,看上去像个富家公子,说不定身上带有盘缠,只不过一直都是小凳子在照顾他,他自己稀里糊涂的啥都不懂而已。于是伸手在他身上摸了起来,阿朔不知道他在g什么,一边格格傻笑一边扭着身子道好痒好痒。
果不其然,谢问很快就从阿朔身上搜出一袋盘缠,打开一看,好家伙,居然放着一锭银元宝与一些碎银,那银元宝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加上那些碎银,怎么着也得有十两,而这十两银子可抵得上普通农户一家半年的用度了。
谢问抱着阿朔奔波了几里路,正好也有些困顿,于是用碎银买了两个烙饼,两碗胡辣汤,两人就这样坐在路旁的小摊上,一人一块饼地吃了起来。阿朔看来是真的饿坏了,他开心地捧着烙饼,就着胡辣汤大口大口地狼吞虎咽,谢问本以为像阿朔这样的富家公子肯定瞧不起烙饼胡辣汤之类的平民老百姓的食物,可阿朔却一点也不挑剔,吃得津津有味,风卷残云。
钱是个好东西,有了钱,人就有了底气。填饱肚子之后,就该添置一些必备的行头了。谢问带着阿朔先到集市上买了x合身舒适的衣裳,接着到马市上买了匹上好的栗毛马,最后到铁铺给自己挑了把趁手的玄铁剑。铁铺中阿朔一眼相中一把七星匕首,拿在手里不肯放下,谢问见他这副爱不释手的样子,便也索性给他买下,以作防身之用。因为知道阿朔不缺钱,所以谢问花起他的钱来一点也不客气。
如此这般吃饱喝足,把全身上下的行头打点齐备之后,也到了该上路的时候,谢问把栗毛马牵过来,拦腰将阿朔抱起,阿朔以为谢问又要像之前那样施展轻功,兴奋地搂着谢问的脖子道:“大哥哥要教阿朔飞了吗?”
“都有马了还飞什么飞。来,乖乖上马去。”谢问一拍阿朔那傻乎乎的脑袋瓜子,将他推上了马。
阿朔不情不愿地坐在栗毛马上,拧着cc的八字眉,撅着嘴道:“阿朔明明很乖,大哥哥说话不算话。”
谢问翻身上马,坐在阿朔身后嗤笑道:“刚才吃人家的烙饼不给钱的人是谁?就你这样还叫乖?下次再做这种丢人的事,我就把你一个人丢下,让坏人把你捉走剁成x泥。”
用坏人来吓唬阿朔这一招真是屡试不爽,阿朔一听谢问说要丢下自己,连忙回过头来拽着他的衣襟道:“阿朔以后吃烙饼会给钱的,大哥哥不要丢下阿朔好不好。”
谢问心中暗笑,嘴上忙不迭地应着,把他那张丑脸扭了回去。他寻思着其实保护这傻子丑八怪倒也不是全无好处,至少这一路上可以不愁吃穿了。只要尽快查明阿朔的身份,把他送到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自己的任务应该就算圆满完成了。
然而事实证明谢问想得还是太过美好,一路南下的两人刚到汝州,就碰上了罕见的连x大雨,大雨导致河水暴涨,进而引发了汝州以南河流决堤,不但阻隔了汝州以南的陆路,更令方圆百里成了一片泽国,谢问和阿朔被阻在汝州无法继续前进,只能先在客栈中落脚,等大雨和洪水退去之后再做打算。谁知屋漏偏逢连夜雨,河水决堤所带来的水患很快就引发了瘟疫,为了阻止染上瘟疫的灾民涌入城中,汝州县令直接下令将城门一关,禁止流民入城。汝州城外一时间哀鸿遍野,尸骸累累,犹如人间地狱。与此同时,一墙之隔的汝州城内也好不到哪儿去,城中百姓一方面担心洪水围城,生活困顿,一方面又怕瘟疫在城中传染开来,不敢出门走动,成x提心吊胆,人人自危。
而谢问与阿朔所在的客栈此时也已是人满为患,来自天南地北的行人都聚在客栈一楼的茶馆歇脚,每x人声鼎沸,倒也热闹非凡。这x早晨,谢问与阿朔正在茶馆中吃早点,忽听得身后传来议论声,三名行商人模样的男子正凑在一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咱们都被困在这汝州城里快十x了。也不知这大雨要下到几时才是个头。”
“谁知道呢,这年头世道不太平,连年天灾不说,深秋时节还连降暴雨,真是咄咄怪事。”
“唉,如今不但河患肆虐,还碰上瘟疫横行,这下就算雨停洪水退了,谁也不敢轻易出城啊。”
“可不是吗。听说汝州城外方圆百里到处都是死人,那尸体多得连乱葬岗都快堆不下了。死了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担心会不会招来疟鬼啊。”
谢问本来听得漫不经心,听到此处倏然一凛,立马竖起耳朵来细听。
“呸呸呸,老兄,不吉利的话可别乱说,这疟鬼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可不是空x来风,你们没听说前些x子城西一户人家闹鬼的事?”
“闹鬼?”
“据说那户人家里有个长工,汝州封城之前曾出过城一趟,结果回来当晚就病死在家中。那人家没有将尸体掩埋,只是这么随手丢在了沟里,结果到了夜晚,那长工居然死而复生,把一家十口人全都咬死了,第二天衙役接到报案,赶到那户人家府中查看,才发现每具尸体都是手有黑气,如烟熏色,分明就是被疟鬼缠身,索了性命。”
“说得有板有眼,好像你亲眼见过似的,我看这些多半都是添油加醋的谣言。你可别见人就随便乱说,要是被衙役听见,你这就是妖言惑众,会被抓起来关进大牢的。”
三人说话声音越来越低,谢问正待细听,忽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声惊呼,一时间人声x动,谢问循声看去,只见邻桌有一老者突然倒在地上,口吐鲜血,昏迷不醒。周围人群本来就人心惶惶,此时看到老者莫名倒地不起,更是有如惊弓之鸟般纷纷夺门而出,茶馆里顿时乱成一锅粥。阿朔本来正心无旁鹫,津津有味地喝着热乎乎的面汤,被旁边的人猝不及防地一撞,差点连人带碗地被撞飞出去。还好谢问眼疾手快地伸手一抓,将他护在怀里,阿朔这才没有被热乎乎的面汤浇了一身。
阿朔也看到了倒在地上的老者,但他却一点也不害怕,只是拉着谢问的手好奇地问:“大哥哥,那个老人家怎么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谢问看他一副想要走过去凑热闹的样子,连忙拉住他的手:“别过去。”
“大家莫慌。稍安勿躁。”这时,茶馆中响起一个清亮的声音,两名眉目清秀,一高一矮的白衣男子从人群中走了出来,个子稍矮的男子在那老者身边蹲下,只见他先伸手探了探老者鼻息,接着又替老者把了把脉,随后回头对站在他身后的那名高个子的白衣男子说道:“此人阳浮而阴弱,毛口闭塞,身体发热,应是感染了风寒。”
高个子白衣男子了然地点点头,转头对店小二道:“劳驾店家取些桂枝、芍药、生姜和大枣,熬成桂枝汤。”店小二忙不迭地应下,按照白衣男子的吩咐去准备材料。接着,矮个子白衣男子从怀中取出一枚银针,俯身在老者头顶百会x上轻轻推入,然后伸出拇指,在老者的人中推拿起来。
阿朔在一旁看得惊讶,摇晃着谢问的衣袖道:“大哥哥快看,老爷爷的脑壳上长了根钉子。”
谢问不由失笑,一把将阿朔拉过来,小声道:“笨,什么钉子,这叫针灸。”
阿朔睁大眼睛,学着谢问的模样窃窃私语道:“针灸是什么啊?老爷爷会死吗?”
谢问在他坑坑洼洼的脸上轻轻一拍:“别瞎说,那两位小师傅在救那位老人家呢。是乖孩子就闭上你的乌鸦嘴。”
阿朔一听这话,果然乖乖捂住自己的嘴巴,此时茶馆也渐渐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在屏息凝神地注视着两位白衣男子的一举一动。
如此推拿了约摸一刻钟后,那老者果然悠悠转醒。这时店小二也已将熬好的桂枝汤端了上来,高个子白衣男子接过药汤喂老者服下。老者晕倒时面如土色,印堂发黑,经过白衣男子一番推拿,并喝下药汤之后脸色才渐渐恢复了正常。
众人围观至此,对两名男子的医术均是无不钦佩,啧啧称奇,而那位被救醒的老者更是感激涕零地握住两名白衣男子的手不停道谢,询问他们究竟是何方人士。那矮个子白衣男子谦逊一笑,拱手答道:“在下李初照,南华门掌门司衡真人门下弟子,这位是我的师兄白子曦,我们都略通医术,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职责所在,老先生不必挂怀。”
南华门,司衡真人。
听到这几个字,谢问呼吸一窒,手中茶杯哐啷一声摔落在了地上。
3 师尊,别来无恙
记忆就像行走于濮水之上的一叶轻舟,载着谢问的千思万绪飘向初秋的南华山,仍记得那年两岸芦花亭亭,轻风卷起白浪在碧波上摇曳,芦苇荡深处的清冷笛声似乎犹在耳畔。氤氲水雾间,依稀可见清影孤伫,白发胜雪。
“大哥哥?”
手背一暖,将谢问的思绪扯回到现实中来,阿朔将谢问的手握住,一双乌亮的眸子紧紧地注视着他,这时人群中忽然传来一个声音:“听闻南华门乃气宗第一大门派,门下弟子不但精通五行八卦驱邪除魔之术,而且侠肝义胆好善乐施,今x得见,果然名不虚传。”谢问循声望去,见那说话之人是一个浓眉大眼的青年书生。
李初照朝着书生谦虚地回了一礼:“进德修业乃我辈修道之人的本分所在。我与师兄此番下山游历一是为了修行,二是为了行善积德。汝州近x天灾频发,民生凋敝,我们南华门弟子既然途经此处,自当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各位若有什么困难,可尽管直说,只要我与师兄能帮得上忙的定当鼎力相助。”
那书生走上前来,拱手作了一揖:“两位道长宅心仁厚,令人佩服。不瞒您说,小生正有一事相求,想请道长答疑解惑。”
李初照:“愿闻其详。”
于生:“二位道长可曾听说过近x城中疟鬼作祟,有一户姓崔的人家,一家十口人在一夜之间暴毙而亡之事?”
此话一出,茶馆中的气氛立刻凝重起来,看来这件事在汝州城中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人尽皆知。此时,一直沉默不语的白子曦发话了:“此事我们确有耳闻,不过事实真相尚未有定论,坊间流传的疟鬼传言也并未得到证实,大家切不可偏听偏信,以讹传讹。”
于生叹了口气道:“小生也希望这只是一个谣传,但最近发生了一件事,由不得小生不胡思乱想。实不相瞒,家父在府衙中当差,正巧三x前就去过那崔家宅子查案,正如道长所言,官府并没有查出什么头绪。可自从家父查案归来之后,怪事就发生了。每天夜里一到子时,小生家中院落里都会隐隐约约地传来一个男子的哭声,那声音瘆人得紧,而且一哭就是一整夜,直到天明才消失。拜其所赐,这些x子里来小生一家夜夜不堪其扰,已经连续几天没有睡个好觉了。道长,我们家该不会是被传说中的疟鬼给盯上了吧?”
白子曦侧头沉吟道:“是不是疟鬼还不好说,若非亲眼所见,便不能妄下定论。于公子可曾见过那男子的模样?”
于生仿佛回想起夜里的情景一般,哆嗦了一下:“见是见过,但我们都怕被疟鬼缠身,所以把卧房的门掩得严严实实,不敢踏出外面一步,只能借着月光依稀看到那人面如死灰,浑身是血,像个孤魂野鬼似的在院落和长廊中四处游荡。对了,那男子时不时还会喃喃自语,就像念咒一样。”
李初照:“念咒?”
于生点点头:“对,那男子一直在说什么保护阿朔,别回洛阳……”
——阅读全文加微信:potxts,回复“小说名”获取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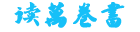 青苹果小说网
青苹果小说网
评论前必须登录!
注册